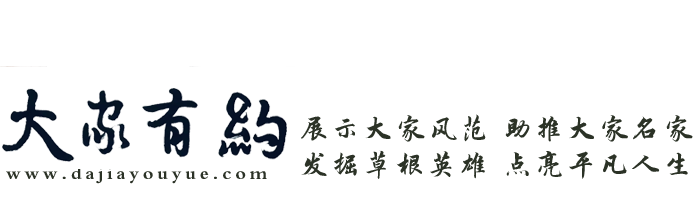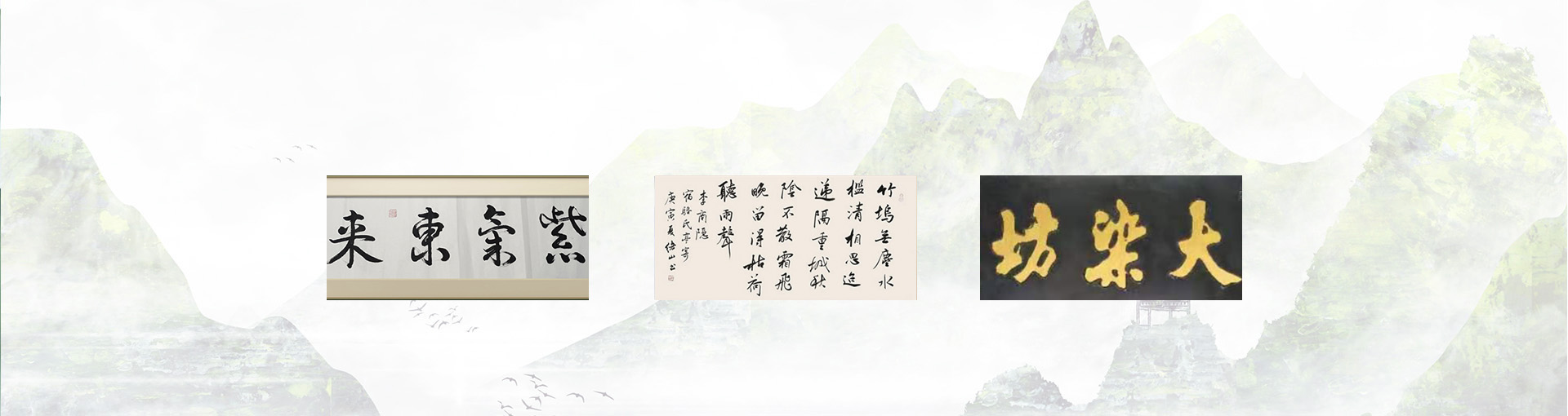|
一沓饭票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四岁的我跟母亲从50公里外的临沂地区水泥厂,回到了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 这里四面环山,道路高洼不平,山都很小,根本没有名字,只是按方向称它为小东山、小南山、小西山、小北山。它阻挡着人们外出的脚步,阻碍着人们极目远眺山外的目光。这样的小山包我们这里很多,大一点有名气的有艾山、卧虎山、九顶莲花山等。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更没草原森林,它土地脊贫,广种薄收,祖祖辈辈憨厚勤劳的人民靠天吃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穷生活,连村里唯一的一座小庙里仅有的一个和尚都供养不起。全村没有一颗树龄超百年的大树,更没有大片平坦的农田,留在印象中最古老的东西是村西头那推起来“吱呀”作响的老石碾。
为什么回来,怎样回来的,当年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如今已经记不起来了,唯一留在记忆里的是我拾了一沓饭票。记得是爷爷领着我去村北方向的园子的路上,在一个巷子中间一棵洋槐树下,我看到了那沓饭票。它用白线系着,一小沓。我忙拾起来交给爷爷,爷爷数也没数,用极快的速度揣进怀里,前后张望了一下,像做贼一样拽着我的手快速离开了那里。 快到园子时,爷爷四下望了望,见没有人经过,便弯下腰来,满脸严肃地对我说:记住了,对谁也别说。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记住了爷爷的话。在那个食物极端匮乏的年代里,这沓饭票的价值,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说它比命金贵,一点都不过分。那时候全民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砍伐树木,砸锅卖铁,全填进了小炼钢炉中,各村办起了大食堂,凭票吃饭。大队规定各家各户的锅、鏊子一律上交,不准私自做饭,如有违反,轻的要挨批斗或游街示众,重的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此,家家户户火不敢生、烟不敢冒,真到了非人的境地。 那时村里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在村食堂干活的姓郑的男劳力,实在饿得不行,偷了食堂里地瓜干面的一个窝窝头,躲到厕所里去吃,正巧被上任不久的年轻的大队长遇上了。大队长夺过半个窝头,揪住那位姓郑的村民的领子,拽着他来到天井里驴拉磨的地方,指着地上的驴屎硬逼他吃。众目睽睽下,这位社员含着屈辱的泪水硬是吃下了一块驴屎。当天他被开除了食堂的工作,第二天噩耗传来,当天夜里他上吊自杀了。 悲剧的产生令人唏嘘。当时社员群众吃光了野菜吃树皮,吃完了地瓜秧吃花生秧,然后吃豆秸和橡子面,吃的人人面黄肌瘦,大风都能吹倒,大人小孩的肚子涨的象小鼓一般,拉不出屎来,多少人没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隔多年,儿时拾饭票的事历历在目,我也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一向本分善良的爷爷,会把我拾的饭票看做天上掉下的馅饼,看做老天爷对我们全家人的恩赐?我们不敢对外张杨,做贼一般,偷偷用它帮全家人渡过最为艰难的时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别说几斤或几十斤饭票,就是一斤地瓜干子,在饥饿难熬的村民眼里,要比现在闪闪发光的金子重要的多。 买红草 一九七四年农历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逢苍山县仲村大集,不满十八岁的我和父亲一起去那里买红草缮屋。 天刚放明,我拉着从大队副业组借来的地排车,和父亲一起去赶集。出了村庄,向南翻过一个小山包,是通往解放路的唯一道路,虽不平坦但能走地排车,是村里通向外面世界唯一的一条笔直的山路。坐上父亲的自行车,手里紧攥着地排车把,用尽全身的力气,保持着既不让自己从自行车上掉下来,又不让地排车脱离了自己的手,看似非常容易的事,做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非常得艰难。山村的道路不是很宽,关健它有石头渣子,高低不平,车轮转动起来的那种颠簸,不亲身体会,你是永远也想象不到的。我担心,有大的颠簸地排车轮子会离开车身飞出去,更担心不小心松了手地排车掉了,也担心自已坐不好掉下来。不管哪种情况发生,我想父亲都会不高兴的,他会说我无能。此时的我用力、恐惧、担心集于一身,唯一的盼望是快点到达集市上。
虽然只有两公里多的山路,拽排车的手已累得又酸又疼,而自行车后包袝架又硌得我腚疼、腿麻、浑身难受,大冬天还热得身上冒汗。这一切艰难困苦全压在自已身上,可又不敢吱声,怕父亲生气,只好忍着。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解放路上。当年它虽是沙土路,但毕竞宽大、笔直、平坦,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不用我全神贯注地防范着。搁现在,弄不好小轿车追到你的地排车上,还得骂你没长眼,碍他的事。 早上八点多,我们来到了集市上。卖茶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汤的,挑水的,合面的,炸油条的,卖火烧的……他们早已来到集市上。集很大,有卖柴草的,有卖牲口的,有卖农具的等等,真是一派繁荣,热闹非凡。 看看天尚早,父亲领着我来到卖丸子汤的摊位上,买了一份丸子汤,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地瓜干煎饼美美地吃了早餐。旁边卖茶的炉灶上,一排坐了有十几把人工打造的薄铁壶,也有沙壶头。烧火用的风箱很大,拉风箱的人不紧不慢,很有节凑推拉着风箱。随着风箱的呱哒声,炉堂里的火苗一鼓鼓地往外窜,烟筒里不时冒岀浓浓的黑烟,一会功夫它们又散得一干二净。早饭后,找个空地把自行车和地排车全放下,我看着,父亲去柴草市买红草。 冬日天短,不知不觉快中午了,父亲没买成,回来嘱咐我继续看着,他又去了柴草市。又过了一会父亲回来时,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位40多岁的老实巴脚的农民。他说他们生产队里有红草,父亲和他谈好了价钱,又是顺路,于是我们便随他去了他村上。后来我知道他们村叫灰疃,在村东头通向我们村路边上一个生产队的场里,那里垛着红草。有几个社员过来帮忙过了称,父亲付过銭,我帮着他装车。 这时太阳就要下山了。我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地排车上,一头系在自行车上。父亲驾着地排车在后,我推着自行车在前急匆匆地往家赶去。由于父亲不长期务农,我又不会装车,因而出村没几里路,车上的红草就散落下来。我们重新把红草装上车,走不几步又散落下来。就这样装了散,散了装,一共没走出五里地,就装了七八次。 这时天己全黑下来。一会儿,满天的星星就出来了,大地象撒了银灰色,一片洁白。路边的树上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只剩下树技子在那里空荡荡的,偶尔摇摇摆摆,似乎在向我们招手,也象在嘲笑我爷俩的无能。偶尔有几棵松树站在那里黑乎乎的,显的很孤独,但象站岗的土兵一样笔挺、尽职。山风吹来,耳边能听到“喔喔”的响声。这时,我和父亲都急了,看看天,看看车上的红草,离家还有十里多路呢。父亲点了支烟,抽了几口,然后对我说:我在这里看着,你回家叫人来帮忙吧。现实情况摆在这里,看来回家叫人来帮忙是唯一的办法了。 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还不太熟练,这样的山涧小道又是石头又是洼坑还是晚上,我真不敢骑,也确实骑不了,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父亲己经决定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应下来。 月亮岀来了,很大,很圆,很美丽,放眼望去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影,山上、坟地里的松树在月光星光的照耀下,远远望去,极像人的影子,看后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发怵。风吹过来,它们在不停地晃来晃去,象喝醉酒的人在行走一般。那时候怕疯人,怕野兽,怕坟地,怕有鬼,尤其一个人走这样的山路真是不敢多想。为了那车红草,为了在山脚下荒胶野外等候的父亲,我只好自已给自已鼓劲,努力不去顾及周边的环境,坚定信心,早点回到家中。 走过了一个叫糊子峪的村子后,就到了临沂县境内,跨过解放路,前面的两个村子就和我们村是一个管理区了。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许多,路也比先前好了许多,路平坦时我就骑一段,路孬好时就推着前行,摔倒了爬起来,来不及拍打身上的草屑和尘土,也不觉得那儿摔的痛,一个信念,早一分钟回到家父亲就少一分钟的等待。终于在10点半的时候我回到了家里,顾不上吃口饭喝口水,先把事情讲给妈妈听。她得知情况后,马上走东家串西家,叫来了本家的大叔二叔等四个男劳力,拿上绳子去迊父亲。 他们回来时己半夜多了,想想当时的情况,现在都觉得心慌害怕,头皮发炸。试想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外的山路上行走,又是无人的夜里,那种孤独感,那种胆战心惊,得需要多大的胆量去克服。几十年过去了,总忘不了那天夜的睛空万里、满天星辰、月光皎洁、银光洒遍山川大地的美好景色,当然也知道了害怕、孤独和寂寞。 最上人恼怒和难忘是,第二天顺红草时,发现红草个子里全掺了白草苗子。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白草是不能缮屋的,一是它不撑年岁,二是肯漏雨。花一样的钱买了烧火用的白草一堆,全家人愤怒、心疼,知道上了那个看似本分憨厚老实的生产队长的当了,骂他不得好死。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他是天生就坏,还是贫穷让他昧了良心? 第一份工作 1974年,高中毕业时,我已经满17岁了,是该为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出力的时候了。 回农村后,我跟着生产队长的屁股后面干了多日的农活。因个子矮小,即便和其他男老力干一样的活,锄一样的地瓜沟,挑一样多的水,可到下午记工分时也只有6分。那种不满,那份不平,那份怨恨,始终折磨着我。离开农村,离开这个穷山村的想法,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大脑里纠缠。农村呀,你是我一天也不愿意待的地方。虽然当时还讲知识青年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那是没有办法,我和我的家人每时每刻都想着逃离这苦难的境地,哪怕它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在外工作的父亲,托了一个在县公路站工作的以前的工友,安排我到县公路站去干临时工,具体工作是到外地去收木柴。虽然是临时工,但一个月能挣37块5毛钱,每天是1块2毛5分,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了。因是临时工,大队要开证明,并规定每月往生产队里交12块钱买工分,到年底不管一个工分值几分钱或几毛钱,你每月交的12元是不变的,它会融汇到全队的分值里去,然后按工分多少分粮食和柴草。往队里交钱的事必须得遵循,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规定的,就连当小工,各行各业的工资也是一样的标准。那时能干上37块5小工的人,肯定得有关系。从那时到现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的延续、发展实际上是社会的悲哀。 去公路站报道后,站里的老苏告诉父亲,让我去费县薛庄公社供销社招待所里,找费县公路局一个姓姚的人联系,他会安排我怎样做好收木材的工作。第二天,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前往目的地。路过探沂时,看到很多冒着浓烟的小窑,父亲告诉我这里和里湖西崖一样烧瓷盆沙壶,因此我对探沂这个地方有了很深的印象。那时滨河大道还没修,我们顺着327国道往西行,走到一个叫严坡的地方再往北走,直到现在的滨河大道临沂至费县境内到头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河,后来知道叫温凉河,我们下游叫岔河,外地人不认识这个字的,只好根据字面的意思都叫他“分河”。在滨河大道的右拐处,有一座通往湖阳、张庄、薛庄等公社的大桥,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只记得是座拱型的石头桥,在桥西边不远处有一个青石砌成的多孔的大石渠,我的印象中应该是从南往北输水的。在来的路上也有这样的水渠,而有的横跨在公路上,后来城乡发展道路拓宽石渠不见了,而眼前的石渠既不妨碍城市发展又不妨碍老百姓出行,所以被保存下来。虽然它是农业学大寨的结果,但他凝聚着当地社员的汗水与心血,它象一条巨龙深情地长卧在温凉河上,默默注视着人间的沧桑巨变人情冷暖,也记载着人们的理想追求,更寄托着无限的祝福,祈盼着一方百姓五谷丰登家业兴旺。 我想现在人们看到它定会想起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今人不能理解的峥嵘时代。几十年后的今天,水渠、大桥依然存在,只是桥上来往的人车不知比过去多了多少倍,而昔日清水滚滚的石渠却静静地卧在那里他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整年整月整日的沉默无语,如果它真的像巨龙一样能腾飞,我想它一定会飞得很远,飞回到那个战天斗地,大兴水利建设的火红年代中去。那个时期祖国大地上涌现了无数条这样的巨龙,可惜的是包产到户后这样的石渠基本全毁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已少的可怜了,过去创造的多少人定胜天的奇迹现在看来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虽然它离我们并非遥远,可还有谁记得它们的过去呢? 到了薛庄公社驻地供销社招待所,父亲和费县公路站来的老姚联系上,把我介绍给他,并当着他的面嘱咐我要听老姚的话,好好干,然后冒着酷暑赶回家去。不一会儿,有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些的小伙子骑车过来,老姚介绍说,他是到这里与我一起收木材的小王,相互认识后,老姚交代了怎样过称,怎样打单子,怎样付款,一再告诉我俩别看差了称,别多付了钱,并叫我过称、打单子,小王见单子付钱,钱多数两遍千万别差了。同时告诉我俩干木柴三分钱一斤,湿的二分钱一斤,不要太长的。安排完后又领着我俩去见了招待所的王主任,让我们吃住在招待所,收的木材放在供销社后面的大院里,有什么难题找王主任解决,最后他把钱交给小王,一切安排妥当后他回才费县去。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小广播,通过公社广播放大站下个通知,把收木材的事进行了广播传达,第二天陆陆续续就有人来卖木柴了,有挑着的、有用小车推着的,络绎不绝。发现有干湿不分的,我和小王叫他们分开,有的太细太长的,我们让他拣出来,他们就非常细心地挑出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争执。他们来买的木柴主要是橡木、马尾松、洋槐等各种杂木,有粗的也有细的,基本没有超过两米长的。一个星期后我们就收了一大堆木柴,小王用供销社的电话机给临沂县公路站的老苏打了电话,第二天站里就派来了一辆五0拖拉机,雇人装上车。下午满满的一车木柴便送到了县公路站。就这样,三天一车五天一趟,我们收的木柴源源不断地拉到县公路站去,钱快用完时,公路站会派个人随着五O拖拉机一同来给我们送来,从来没耽误事。 不知不觉中,我们在那里己收了两个多月。我和小王在一起工作中得知他是老姚的小舅子,叫王玉庭,他家就是南边湖阳公社的,今年21岁,初中毕业后已找了对象,说好年底结婚的。在招待所,我们还结识了伙房的男青年小崔和小贺,认识了女服务员小马和小王,并知道小崔小贺小王他们是供销社招的亦工亦农,而小马是下过乡的,招工后是正式职工。那时我们很单纯,没有现代人的眼界和知识,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混得像亲兄弟姐妹一样。记得当地供销社还设有图书馆和照相馆,图书馆里有个姓党的阿姨,据说一次生了三胞胎,我感觉到很惊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知道在我们村上有生双胞胎的,从来没听说过生三胞胎的。她不光生了三胞胎,而且姓也很特别,姓党,中国共产党的党。这两件事让我长了见识,知道了妇女不但能生双胞胎,也能生三胞胎五胞胎,更知道了人们不光有姓张、王、李、赵的,还有姓党的等等。 清早,我和小王穿过院前的一条公路来到斜对面的一条大河边上,叫什么河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大片的沙滩,有雾气升腾的河面,水中有成群的鸭鹅,有上蹿下跳的小虾,有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小鱼儿。当地村民从河里往家担水,不远处村子里升起袅袅炊烟,浆洗衣服的姑娘大嫂大娘们也许正忙着摊煎饼做早饭,还没来得及下河呢。 王玉庭离家不远,几天可以回去一趟。我从7月底来后,直到8月底才回家一趟,那还是跟了拉木柴的五0拖拉机先到了临沂县公路站,然后老苏领着我到南边的解放路上拦一辆往城里运送石头回去的小驴车,让他们捎上我一段。有时能拉到离我家近一些的马场湖,有时到城前,下了驴车后,不管天黑不黑,路途多远,我去都得凭着两条腿走回家去。想想现在,看看过去,离开机动车有谁还会走着回家呢?而且还是山路。记得第一次回家时,我还买了二斤很新的鲜栗子,还向前来卖木柴老大爷要了一根檀木的镢把,那种得意,无以言表。 那年的八月十五,我没捞着回家,一个人在供销社的招待所里度过。当天下午小王骑车回了家,我在供销社前边的街上闲逛,招待所的王主任看见了,告诉我晚上别到招待所食堂吃饭了,他们杀了羊让我等着。回到招待坐在在床边,想家想亲人的感觉在脑海中转来转去,毕竟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亲人。中秋节到了,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吃上月饼,吃上水饺?虽然自己盼着中秋节的到来,可到临了却是一个人漂泊在外,与家人的消息全无。那种寂寞,那种孤独那种无可奈何,一起涌上心头。天黑了,在王主任的安排下,小王小马两个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香喷喷的爆羊肉和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馒头。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达应该是,这是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现在想这孤独、这寂寞,这无奈是便我成长的基础,更是我独立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有一次从家里回来,因为缺少换洗的衣服,妈妈让我穿了她的一件褂子。因为家里穷,自己也还小,当时没有感到什么不妥,可到了招待所,小王小马就问我怎么穿了个女人褂子,穿谁的。我告诉她们,穿妈妈的,虽然她们没有过多讥讽,但使我明白了男女衣服有区别,是不能乱穿的,觉得怪丢人的。可想想那个年代又有谁没穿过大人的衣服和带补丁的衣服呢,这些全来自一个“穷”字。 两个月后,我被招回到县公路站里,然后被安排到马场湖、中桥一带收石子,收木柴的扫尾工作由王玉庭一人来完成。后来我才知道,收木柴和收石子都是为了铺从现在的九州商厦门前至临西八路这一段解放路的。因为那时它还是沙子路,而且解放路当年是从临西八路向南拐然后通过针织厂、国棉八厂后往西拐再通向马厂湖一带的,现在取直了,沙子路变成了柏油路不说还修了高架,发展的速度真是日新月异。 后来我有幸到临沂银行上班,在城里见过小崔小贺他们,他们是来采购伙房设备的,王主任、王玉庭和两个服务员都没见过。那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马,据说当了农行的协储员,后来调到临沂来了。有一次在东方红电影院北边,我看到了一个人极像她,高声的喊她,喊了多次,她头也没回,我怕认错了人没敢追上去,任她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一晃50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工作、婚姻家庭、身体状况乃至他们的命运怎样?我一概不知。有时会想起这段往事,追忆着和他们交往的日子,追忆着这并非遥远的历史,追忆着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含泪奋斗的历史脚步。 |